看《沈从文的后半生》,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师晚年的几次哭泣。
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回忆:“一次母亲见他独坐在藤椅上垂泪,忙问怎么回事,他指指收音机——正播放一首二胡曲,哀婉缠绵—奏完,他才说:‘怎么会……拉得那么好……’泪水又涌出,他讲不下去了。”
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,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,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,流下泪水。不知道为什么,我看完整本书,很多都遗忘了,只有这个场景却定格在我的脑海。
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。
张允和在《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》里提到:“1969年,沈从文下放前夕,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,“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,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:‘这是三姐(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)给我的第一封信。’
他把信举起来,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—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,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又伤心又快乐。”
越到老年,沈从文越爱流泪。
一九八二年回乡听傩堂戏而流泪,生病后在家里,偶然听到“傩堂”两个字,本来很平静的他,顺着眼角无声地落泪。
一九八五年,一个杂志社几个人来采访,问起“文革”的事,沈从文说,“在‘文革’里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,特别是女厕所,我打扫得可干净了。”
来访者中有一个女孩子,走过去拥着老人的肩膀说了句:“沈老,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!”没想到的是,沈从文抱着这位女记者的胳膊,嚎啕大哭。什么话都不说,就是不停地哭,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。张兆和就像哄小孩子一样,又是摩挲又是安慰,才让他安静下来。
有人觉得这样的沈从文颠覆了他们对“大师”的认知:一个七老八十的文学大家,怎么能还那么爱哭鼻子呢?也有人说,这是一个大师的哭泣。
但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个老人不加伪饰的真实和“自我”。
《沈从文的后半生》作者张新颖说,沈从文身上最吸引人的,正是他的“自我”。
“有了这个自我,他就不会随波逐流。因为有一个本能、最本真的东西。他从这个角度出发,来判断时代,判断人和事情,就不会为流行的、主流的观念和思想所左右。沈从文看任何东西,角度都会和一般人有所不同。
他有这个能力,随时能跳出来。我们没有,所以总是被强大的时代裹挟着。”
沈从文后半生封笔四十年,与文学交道并不多,但受他文字影响并喜欢他作品的人,却越来越多。
近年来声名大噪的“不老的老头”黄永玉,他所写的《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》,“就是沈从文召唤出来的,算是弥补他未写完的《长河》的遗憾。”
还有著名导演侯孝贤,1982年拍摄《风柜来的人》时面临很大困惑,踌躇之际,他读了朱天文给的《从文自传》,豁然开朗。
“一个人可以承受那么苦难、那么恐怖、那么血腥的故事,可是即使有这样的故事,在太阳下面还可以看到温暖,还可以看到人性的美好,人的胸怀还可以亮一点,更大一点,由此建立了侯孝贤拍电影的自觉。”
张新颖认为,后来侯孝贤拍的《悲情城市》,很明显可以看到《从文自传》的影子。
沈从文在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为他出的作品选中自序道:“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。”
听起来真令人伤感。但是显而易见,这句伤感的预言并没有应验,正如他的妻子张兆和在他去世之后才理解他一样,他的作品也在慢慢地,慢慢地被更多人读懂。
“强大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,而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,走到今天和明天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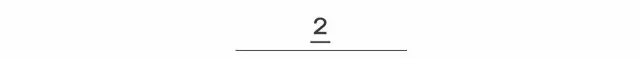
沈从文,原名沈岳焕,1902年12月28日出生在湘、川、黔三省交界的湘西小城凤凰。
凤凰城是苗族、土家族、汉族聚居区,两百多年前清政府为了镇压与虐杀不服从统治的苗民,派了一队兵驻扎来此,才形成了一个城镇。那个时候的凤凰,到处是碉堡、军营,居民大多为戍守的军人。
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,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苗民的反抗,血染红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。沈从文说,他走过的每一寸的土地,脚下面都是血。
到如今,一切完事了,碉堡多数业已毁掉,军营也多数成了民房,但当地崇兵尚武的彪悍民风依旧存在。
沈从文的祖父沈洪富曾做过一度云南昭通镇守使,同治二年又官至贵州提督。父亲沈宗持也是行伍出身,一心想当将军,但时运不济,正赶上清王朝的没落。

对朝廷彻底失望的沈宗持直接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起义,后来又到北京,与人谋刺袁世凯。事机败露后,被迫亡命关外多年。沈家由此开始败落。
他的母亲黄英出身于书香门第,年纪极小时便随同长兄在军营中生活,因此见闻胆识都在一般女子之上。沈从文兄弟姊妹的初步教育,便全是由这个瘦小却通达的母亲担负的。
沈从文从小就习惯了看杀人。上学的时候,走过杀人的地方,昨天被杀的人还没来得及收尸,尸首被野狗吃了,只剩下一块头骨,他就走过去瞄瞄,或者拾起一块小石头敲打一下,看看还动不动。
他甚至还见过这样的景象,看见十几岁的少年挑着担子,担子前面放着他父亲的头,担子后面放着的是他叔叔的头。
他6岁进私塾,然而那呆板无趣处处受牵制的读书生活使他厌倦,而爬树、游泳、钓鱼、捉蟋蟀乃至逛街、打架,却使他感到身心愉悦。至于凤凰城里那些五花八门的作坊、店铺,那些辛勤劳作的人们,更能引起他无穷的兴趣。
幼时的这些见闻经历,都为沈从文日后写作提供了许多灵感与帮助。
由于家中有吃粮当兵的传统,加上其野性难驯,1917年8月,刚刚14岁的沈从文,就被母亲以补充兵的名义送去当兵,让他到社会上去学习生存。
离开了家中的亲人,向什么地方去,到那地方去又做些什么,将来有些什么希望,十四岁的沈从文对此一无所知。他像只被放飞的笼中鸟,对外面的世界充满着憧憬,对眼见的一切都觉得新奇、快乐。
他随军一路走遍了沅水流域,领略了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,饱览了各处迷人的自然风光,为他以后描写湘西风情的小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与此同时,他也亲眼目睹了更多的杀戮,仅在怀化镇一年零四个月期间,就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。又看到军队各派系之间明争暗斗的种种勾当,使他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疾苦有了更深的了解与同情。
到目前为止,我们可以看出,沈从文的整个青少年时代,都是在恐怖、血腥的环境中度过的,这些东西,对一个人的心灵会产生怎样的影响?
正常来说,近墨者黑,沈从文应该会变得心狠手辣十分残忍才对,但是他却恰恰相反,即使在那杀人不眨眼的世道里,他的心也总是柔软得很,总那么容易被美好的事物打动。
当身边的军士们每天除了“杀人”或者“看杀人”再无事可做时,他却喜欢跑到河滩上去散步。
水船斜斜地孤独地搁在河滩黄泥里,小水手从那上面搬取南瓜,茄子,成束的生麻,黑色放光的圆瓮。那船在暗褐色的尾梢上,常常掠得有朱红裤褂,背景是黄色或浅碧色,一派清波,一切皆那么和谐,那么愁人。
美丽总是愁人的。每每见到这种光景,沈从文总是默默注视许久。他要人同他说一句话,想要一个最熟的人,来同他讨论这些光景。他想要找到一个温暖的人,可以跟他一起来对抗那些黑暗、残暴、绝望的东西。但是他找不到这样一个人。
心中怀揣着对美好世界向往的沈从文在残酷血腥的现实生活中,是那么地寂寞。他开始隐隐约约对于身上的灰布军衣感到厌恶,与家人分离的痛苦忧愁,第一次涌上了他的心头。
20岁那年,沈从文离开旧部队投到了“湘西王”陈渠珍部下,因为认得几个字,他被分派到陈身边做书记。
陈渠珍虽是行伍出身,却喜好读书,尊重文化人。他不仅有大量藏书,还收藏有历代名画、古磁、碑帖、铜器等。沈从文每天的工作,便是为陈渠珍查阅、抄录书中的材料,并且为那些书籍归类编号,为旧画、古董作登记。
这一工作不仅使沈从文得以阅读大量书籍,提高了他的文学素养,同时也启蒙了他对古文物鉴赏的兴趣,为他晚年进入历史博物馆做杂文物研究埋下了伏笔。
生命其实是很奇妙的,我们今天所有生命呈现出来的面貌,都与我们的过去相关,而现在所经历的一切,也决定着我们的未来。
到了这时沈从文的性格似乎也稍稍有了变化。不管去哪儿,他总拿了一本书。
那时候,沈从文一个月大概领3块钱的补贴,但有谁能够想象,在这个小兵的包袱里,有一份厚重的“产业”:一本值6块钱的《云麾碑》,5块钱的《圣教序》,值两块钱的《兰亭序》,值5块钱的《虞世南夫子庙堂碑》……
沉溺于书本的沈从文求知若渴,他日益感觉自己知道见到的太少,应知道应见到的还有太多,怎么办?必须进一个学校,去学些自己不明白的问题,得向些新地方,去看些听些使自己耳目一新的世界。他渴望变得更好,让自己成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。
“智识同权力相比,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。”沈从文如此下定决心,要去北京读书。
当沈从文把这点打算告诉陈渠珍时,陈拿了三个月的薪水给他,并鼓励他说:“你到那儿去看看,能进什么学校,一年两年可以毕业,这里给你寄钱来,情形不合,你想回来,这里仍然有你吃饭的地方。”
于是,二十一岁的沈从文,怀揣一本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只身一人,冒冒失失跑去了北京,在北京大学当了一名“不注册”的旁听生。
但是,原先陈渠珍答应提供的资助不久成了泡影,他在北京的求学生活一时难以为继。
他寄宿于湖南会馆,冬天没有棉衣,没有火炉,严寒难耐,只能用被子裹着身子坐在桌旁写作。为了生活,他不断向报纸杂志投稿,却一次次被退回。迫于困境,他给当时蜚声文坛的作家郁达夫写信求助,很快便得到了回应。
接信后,郁达夫冒着冬夜的大雪,前来探望沈从文。他默默地听着沈从文倾诉自己来北京的打算和目前的困境,内心波澜起伏,“我看过你的文章......要好好写下去。”
彼时会馆的大厨房里,正传来师傅炒菜打锅的声音,不一会儿,空气中便弥漫着饭菜的香气,勾得人饥肠辘辘。
“你吃饭了没?”郁达夫问。
“没。”
郁达夫站起身来,将围在自己脖子上的羊毛围巾摘下,掸去上面的雪花,披到沈从文身上,然后邀他一道出去吃了饭。结账时,共花去一块七毛多钱。郁达夫拿出五块钱付了账,将找回的三块多全塞给了沈从文。
两人作别后,回到住处的沈从文禁不住伏在桌子上痛哭起来。郁达夫的雪中送炭,不仅缓减了沈从文生活的困顿,也让他坚定了继续在北京写下去的信心,最终名动京城。

1923年,踌躇满志的沈从文挟着铺盖在北京前门车站下火车。月台上的边城青年对眼前这座豁然敞开的古老城市说:“我是来征服你的。”
但是二十多年后,这座城池却差点将他倾覆。
当时,坚决不肯投身于某一个集团之中的沈从文,被台湾人骂,也被国内的人骂。在那个特殊年代里,人们对待是非的判断是那样简单粗暴,你不跟我站到一边,那你就是帮助敌人。
你越有一定的影响力,你不跟我合作,那你就是最应该被排斥的人。在这种情况下,想保持一种独立选择和独立人格是非常困难的。
只读过小学、湘西行伍出身的“乡下人”沈从文,四十多岁时已经写出七十多部作品,名噪一时,雄心勃勃。然而在人生的下半场,他毅然宣布封笔来维护自己用笔的自由。他写作,就要按自己的想法来写,按照命令或按照规定来写,他写不出来。
《无从驯服的斑马》是沈从文写于1983年春的一篇未完成的作品。
他在文中这样总结:“就我性格的必然,应付任何困难,一贯是沉默接受,既不灰心丧气,也不呻吟哀叹,只是因此,真像奇迹一样,还是仍然活下来了。体质上虽然相当脆弱,性情上却随和中见板质,近于‘顽固不化’无从驯服的斑马。”
对于当时的任何一个作家来说,写或者不写,都由不得自己,都完蛋了。一般人都跳不出这个圈子,但沈从文从写和不写之间跳出来了,找到了另一个要做的事儿。
那件要做的事儿便是——成为一个不起眼的杂文物研究者、解说员。数十年的漫漫岁月里,他克服了外在条件的艰难和内心的痛苦,在这一领域筚路蓝缕,于喧闹暴戾之中,始终独善其身。
学者傅国涌描述,“以后的三十年,中国少了一个作家,而北京午门下多了一个指点解说、抄写说明的老人,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就是其中的结晶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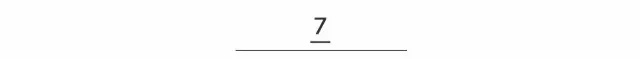
在紧接着的那特殊的十年岁月里,沈从文的住房被占,家被抄了8次;书稿图籍、文物什物或遭掠毁,或当垃圾卖掉。他曾被分配打扫博物馆的女厕所,下放期间饱尝事业凋敝和旧疾之苦。这一切,都被他用幽默乐观的态度,对美的细腻体察,一一消化。
据黄永玉回忆,当时某一天,久未见面的叔侄俩忽然在东堂子胡同迎面相遇,沈从文装着没看到他,擦身而过。一瞬间,他头都不歪地对黄永玉说了4个字:“要从容啊!”
还有一次,他跟沈从文从东城小羊宜宾胡同走过,公共厕所里有人一边上厕所一边吹笛子,是一首造反派的歌。沈从文说:“你听,‘弦歌之声不绝于耳’!”
干校期间,他从咸宁迁到双溪,辗转劳顿,血压陡升。他还给黄永玉写信:“这里周围都是荷花,灿烂极了,你若来(一定喜欢)……”

晚年回凤凰老家,住在黄永玉的老屋里,他很喜欢那座大青石板铺的院子,三面是树,对着堂屋。早上,茶点摆在院子里,雾没有散,周围树上不时掉下露水到青石板上。
黄永玉对他说,“三月间杏花开了,下点毛毛雨,白天晚上,远近都是杜鹃叫,哪儿都不想去了......我总想邀一些好朋友远远的来看杏花,听杜鹃叫。有点小题大做......”
“懂得的就值得。”沈从文闭着眼睛,躺在竹椅上回应。
黄永玉始终不明白,是什么力量使沈从文把湘西山民的朴素情操保持得这么顽强,又是什么力量让在寒凉世事中浸泡的沈从文永远这样热泪盈眶?
沈从文14岁从军,看惯了残酷血腥的杀戮,21岁北漂,一生遭遇了无数白眼冷遇。但是他在后来的写作中,却打造了一座与世无争的边城,塑造了一个个单纯清澈的灵魂。
阴风冷雨的现实,生命沉沦山河破败的时代,没有摧毁掉他对人生的希望与热爱。他用他赤子的心来抵抗人性的冷漠与麻木,用他的笔来呼唤美好善良,用他的文字将世人从恶劣、残暴的现实环境中拯救出来。
千千万万在黑暗中挣扎的人,因了这文字散发的光和热,感受到希望,感受到温暖,感受到平静又长久的爱的力量。
1988年5月10日晚上8时30分,沈从文静静地走了。葬礼遵其遗嘱未放哀乐,而改放贝多芬的《悲怆奏鸣曲》——他生前最喜爱的音乐。
“不折不从,星斗其文,亦慈亦让,赤子其人”是他逝世后,傅汉斯、张充和从美国电传来的挽辞。采用嵌字格,尾字连起来是“从文让人”,巧妙且贴切地概括了沈从文的一生。
 社会教育
社会教育

 如何培养孩子兴趣爱好?家长自己做到这三点!家长真该好好听听!
如何培养孩子兴趣爱好?家长自己做到这三点!家长真该好好听听!












